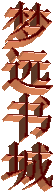
混沌加哩咯楞 第五章
走到人群最拥挤的地方,男生就乘机往女生身上靠、挤,女生发出兴奋的尖叫,
满大街都是喜气洋洋的大人、小孩儿、青少年,浑身发热地挤来挤去。
红旗比着高大,标语比着书法。
又是“大喜日子”,又是游行,冲着窜到天上的“二踢脚”又一通傻乐。“庆
祝!!……”
“狗崽子!”突然一颗弹弓纸弹打过来,登时耳朵发麻红旗也失去了光彩。我
都忘了这个茬儿了。
转头看看其他的“狗崽子”,其中一个因为不敢去厕所怕挨打,已经把尿尿在
裤子里了。尿顺着裤腿儿往下流,腿上结了冰她还仰着脸冲着被灯火照亮的夜空傻
笑。
我们中学的大旗在无数旗子中并不显得难看。
嘣--- 嘣!又是一个二踢脚。我真年轻呵,我真灵活呵,我真能跑呵,我真能
挤呵,我真能喊呵--- “狗崽子!”头上又挨了一颗纸弹。
这回我想哭。队伍里开始唱革命歌曲大轮唱。
唱着唱着就忘了疼。
游行结束后老师让我们女生连夜绣出一幅领袖巨像来,男生连夜写出一百幅大
标语,有人当场把手指尖儿用大头针扎破写“血书”。
我们中学好像是老修道院改装的。“文革”后废除考试,全“就近入学”,简
直是老天爷开眼,上学跟去游艺场那么轻松。教学楼是个老破洋楼,每分钟地板都
在响,脚一踩在上面楼板就打颤。楼上的教室洒水,楼下的教室就下雨;楼上的教
室有人打架,楼下的教室就地震。除了最高层最高处那些镶在楼梯拐角处使劲儿抬
头才能看见的彩色玻璃仍旧顶着风雨,其他教室的玻璃全部打碎了。风在教室里玩
儿障碍赛跑,我们穿着棉鞋棉袄棉候棉手套,缩在教室里背语录,英文的第一课是
“Long Life Chairman Mao”,第二课是“Long Long Life Chairman Mao ”,下
了课浑身都长满冻疮。
因为“就近入学”,同学们都来自同一地区,好像互相全认识。女生大部分穿
花格子上衣背花布书包,谁要是稍一特殊,就是一片“啧啧啧”。“啧啧啧,她穿
了一件的确良上衣,都快透明了!”“啧啧啧,新尼龙袜。”“啧啧啧,一身国防
绿!”男生呵女生绝不说话,可他们互相知道任何一个人的底细而且谁活出一个新
闻来都逃不出去大家的嘴。谁谁谁的爸爸从前卖烧饼现在是工人;谁谁谁家原来有
个小铺后来归了公;谁谁谁的爸爸是地主马上要回乡下;谁谁谁的妈妈是“破鞋”
······
领袖像是用塑料窗纱衬底用嘿粗线绣的,绣起来一点儿不难,在窗纱上用线织
出一个个黑“X ”子,黑“X ”子就组成了一幅巨大的领袖像,绣的时候不耽误用
嘴聊天儿用耳朵听闲话。
我们班小组长带头说起班上的大秀,大秀在她小学五年级时就被男生们“强奸”
了,后来又被她爸爸“强奸”过,后来她去靠和男人“胡搞”给她爸爸赚烟酒钱。
她家只有一张大炕,她爸和她妈睡这头,她和她的男人睡那头,在城里有炕的人家
不多。
我听哥哥说过在《初刻拍案惊奇》上有那种“入港”的事,但哥哥不许我看这
本书,想起小汀说过男女在一起不过是“接吻接吻接吻”,而《红楼梦》也只说是
“云雨”,可能“云雨”就是“接吻”,“接吻”就是“入港”吧。
“她连口罩都买不起,有次我发现她的胸前只挂了一根口罩带,然后捌在衣服
里愣装着是带了口罩,让我一把给揪出来,当着大伙让她现了一回眼。”小组长说。
她以“敢向坏人坏事作斗争”而闻名。
“我听说凡是流氓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女生撇着嘴说。
“看哪儿?”另一个问。
“看屁股。流氓的屁股都往下垮。”那女生继续撇嘴。
“哟,真怪恶心的。”另一个说。
“咳,别提了,我们家邻居就更不象话了。两口子晚上干那事也不关灯,惹得
院儿里的小孩到晚上就趴在窗外边透着一个破窗户纸洞往里看。”又一个女生连笑
带比划。
“真恶心,真恶心死了。反正咱们班肯定还有更多的流氓。”小组长说。
“谁呀?”
“咳,我就不说了,你们自己想吧。”小组长故意闭上嘴,弄得所有人都紧张,
开始互相怀疑,也怀疑别人知道了自己什么。我也怀疑他们知道我在看《红楼梦》。
“什么算流氓啊?”一个女生小声问。
“你仔细想想,有什么是不能坦白,不能光明正大,和什么男人有什么不正常
的交往全算。”小组长压低声音说。
“有回我坐火车,挨着一个男的坐了一晚上,我们俩全睡着了,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我的头搭他肩膀上了,这算不算和男人睡过觉?”那女生问。
“当然算,说不定你以后该有孩子了。”小组长挤着眼睛笑。
“呵?”那女生傻了。
没人说话了,只低头飞快地绣那个像。可能所有人都有“流氓”史,都怕说出
来,也怕站起来让别人突然指出自己的屁股是往下垮的。
“三月里来是清明,姐妹二人去踏青,随带着放风筝。
风筝上去虚空里转,麻绳拉着手腕疼。疼得很呀。
可恨老天爷刮大风,刮起大风吹断绳。
真是一场空。哎哟……“大表姑唱。
“你大表姑是你们家的人吗?”
大表姑自称是孔子的后代,爸爸自称是蚩尤的后代,大表姑姓孔,爸爸姓黄,
水知道他们的姓是真是假呢?
爸爸肯定在说谎,蚩尤长得像牛爸爸长得像羊,怎么可能是一家子?但大表姑
真长了孔子的牙,倒使人不能不信服。她说孔家是世代长子相传,传到她这一代就
连孔家的汤的汤的汤的汤也喝不上了,除了只落个姓“孔”,她爸爸的爸爸的爸爸
就早已是世代扛长活的了。所以她骄傲的宣布她是“世代贫农”。
大表姑年轻时不知为什么到了城里,托人找工作找到了她的堂弟,堂弟又找她
堂弟的干哥,干哥正好是爸爸的妈妈的表嫂的干儿子。就这么“堂”的“干”的
“表”的全用上了,大表姑就来到了我们家,从我一睁眼就看见大表姑在我面前
“抓挠儿”,我以为她是我妈,后来才知道她叫“大表姑”,后来所有人都问我大
表姑是不是我们家的人。
爸爸自杀后,大表姑变成了家里的爸爸,妈妈什么都听她的。连两个人的长像
都愈来愈靠拢,不知是谁往谁那儿靠,反正她们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竟变得快成双胞
胎了。
妈妈是个土军阀的女儿,十八岁以前不知哪天,姥爷开了洋荤,给她请来个大
城市来的留洋学生当家庭教师,没出两个月,她就带着一脑袋俄罗斯与法国革命的
幻想穿着缎子旗袍逃出了她住的那个小镇上了延安。那个家庭教师也失踪了,姥爷
以为他俩私奔了,可四九年后姥爷见到的女婿不是家庭教师而是爸爸,他才松了口
气下到黄泉。他恨死了那个家庭教师,后来听说家庭教师在前线是被炮弹炸碎了又
心疼起他来,但还是庆幸妈妈没嫁给他。妈妈带着幻想穿着墨绿色缎旗袍到了延安
后,凭着一双大眼睛进了文工团。文工团的女兵大多来自城里,不光能说能唱能蹦
能跳,还能用土染料把军装染成黑的,再自做一双黑布鞋披上一条自染的土布围巾
号称是现代的“安娜”。她们走在街上引人注目,决不甘于用军人生活淹没女性。
这种“安”式风度一直跟了妈妈一辈子,直到她已变成了一个圆陀螺,提起“安娜”
形象她仍能挺胸仰头目不斜视。
“哈哈,你应做一朵牡丹。”她提醒我,看着我的牛仔裤。
“我是一颗狗尾巴草。”我用唾沫擦擦裤子上的污迹。
“安娜……”她又要说。
“我没那么细的腰!”我说完就走。
妈妈前半辈子基本是在梦里活着。“罗亭”、“安娜”、家庭教师教她会说了
“my darling”,“love”就永远“bye-bye ”在前线献身了;这简直是一首诗,
从此妈妈的英文就停留在“darling ”上。后来的“darling ”是爸爸,一表人材,
又是出生入死累计战功;虽不似前一个那么诗意的天生一个“英魂”,但后者更显
坚实可信、思想成熟。借了爸爸的光,妈妈一结婚就有了特殊待遇, 不在只是穿
了一身黑军装在河边唱歌的“安娜”了。她有特殊的食品供应、行军时骑驴。后来
进了城,前呼后拥,司机警卫加厨师,“妈妈你这么革命倒挺舒服。”我说,“胡
说,能参加革命的都是不怕死的。”妈妈的朋友提醒我。我当然服输, 她们全是
香气扑鼻穿着绣花衬衣高跟鞋的“人物”,我算老几?妈妈从来没对我满意过,一
会儿嫌我胖一会儿嫌我瘦,让我学跳舞、逼我早起练功、练来练去到了舞蹈学校老
师拿个尺子从脖子量到屁股根儿、又从屁股根儿量到脚底,说下半部分应该比上半
部分长三寸,而我纸长了两寸半,还差半寸没地方去找!妈妈才罢休。又让我学唱
戏,早起吊嗓子,像杀鸡一半;最后老师说这孩子嗓子有咽炎最好别唱。妈妈又让
我改学画画儿,反正她不让我安安稳稳过日子,放了学跳足了猴皮筋儿。
“你可以成为一个天才可惜你不用功。”妈妈说。
“我的腿不够长,我的嗓子有咽炎。”我反驳。她一点儿也不考虑她把我的腿
生短了半寸。
“画画儿用不着腿长吧?”她像弹钢琴那样敲桌子。
“我可能是色盲。”我得意地说。真希望让医生确认她生的这个孩子一无是处,
我的后半生就安稳了。妈妈一心认定她的孩子必须是个什么。
“你生下来以后专门在医院里作过各项检查,医生说你在各方面都比别的孩子
长得全。”她看着我。
全?什么叫全?
“可惜白生了!”她叹口气,不再看我。
白生了?什么叫白生了?
妈妈在文革的经历才使她变成了个“妈妈”。她一下老了,白头发突然出现,
头发直了,垂在脸前,脸上的肉松了,眼睛也小了。眯缝着眼看我,不再用手去弹
桌子面。看着她那副样子,让我跳芭蕾舞唱戏吊嗓子干什么都行,只要她再变成
“安娜”。但没准儿哪天,她那股“安娜”劲儿又来了,我只好再逃。
至于大表姑,大家都说她是个“全乎”人,在乡下的时候被看成是吉利干净的
象征,混丧全请她帮忙。可她一辈子没有过男人,也不知怎么就落个“全乎”。有
本书叫《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可我大表姑一个人就“全乎”了。
“起床啦……吃早饭啦……上幼儿园啦……今儿梳什么样的头呀?跳荷花舞那
样的吧……瞧,新连衣裙,百褶的,转圈儿……哟,跟大伞似的。”大表姑拿我当
她的模特儿。
“大表姑我们在幼儿园转圈儿比裙子大的时候,男生就趴在地上往上面看,就
像这样儿……”我学。
“哎哟可不得了,坏孩子。跟男孩儿玩儿的时候可得当心。”
在幼儿园玩了一天“揭发小朋友”,晚上回家做梦梦见抓特务。早晨醒来遍地
是落花。
“看院子里多好看,去演< 黛玉葬花> 吧。”大表姑塞给我一个小花篮儿,给
我梳了一个唱戏的“小姐头”,穿上新做的连衣裙去院子里“葬花”。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什么来着?大表姑?”我刚扭两下就忘了。
“有谁怜?”大表姑早就把花替我扫好了,放进我的小花篮儿里。
“有谁怜?下面什么来着?……”我一扭台步就忘了词儿。
“游什么来着?”大表姑反过来问我。
“哦,对了!游系软系飘春系,落系轻沾扑绣帘。闺中女儿惜春暮,忍踏落花
来复去,明年闺中知有谁,不管桃飞与李飞,一年三百六十日,花落人亡两不知!”
我一边扭台步,一边胡唱。
“这么快就唱完了?你这孩子乱唱!”大表姑干脆拿把大扫帚吧花瓣“吭吭吭”
几下全扫在一起了。
“埋吧。”她说。
“大表姑,我这衣服也不像啊,干明再做一身唱戏的衣服给我吧。”我提着我
的“千层百褶裙”。
“干明咱不唱林黛玉了,太悲切,咱赶明儿雪杨贵妃了。”她把花瓣撮进簸箕
里倒进垃圾箱。
“林黛玉跟贾宝玉好是么?”
“那都是老话了,旧社会的事,现在这么大点儿的孩子不兴谈这个,出去别乱
说。赶明咱学唱《杨家将》了。”
大表姑有一箱子处理品,皮鞋、布料、手表、皮包、毛衣、绸衫……她在过节
或带我出去逛商店时穿,全穿上还是看起来像“世代贫农”。
她看小人书但是会背唱词。还懂得戏。他只要去一次饭馆就会做那儿的菜。她
看一下画报就会模仿并设计新服装。如果拿时候有“Christian Dior”,她会仿造
一系列“Dior”产品。
她以她的“全乎”自豪,一辈子主张“男女授受不亲”;她为妈妈和爸爸在一
块儿睡觉而害臊;她说我出嫁前最好别跟男孩子说话;“除非你跟他定了或者我看
他不错。”什么叫我跟他定了她看着不错?我不说话怎么“定”?她看着不错管屁
用。
所以等杨飞跟我好了十年最后决定不当我“丈夫”时,我飞快地就叫大表姑和
妈妈一起为我跳了一个她们看着“不错”的,飞快地结婚有飞快地离,弄得她俩看
着我的时候跟看“处理品”似的。
妈妈和大表姑两人愈长愈像,就一起穿套裁出来的一样的衣服。有时你能看见
两个圆滚滚的蓝或两个圆滚滚的灰;有时你能看见两个圆滚滚的透明麻布衫;一个
里面透出断了带子的破胸罩和两个垂在肚子上的乳房,一个里面透出比肚子矮一截
的两个处女似的小乳头。妈妈的房间里有烟味儿还有书,大表姑的房间里有廉价花
露水味儿还有个今天穿牛仔裤明天穿起超短裙的小洋娃娃。
“头一年栽花花没成,
第二年栽花霜皱了,
第三年赶上发大水······
哎哟我的妈……“大表姑唱。
“你必须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娃子对我说。
她老是有她的生活方式。小学是梦想做大使夫人,穿的衣服全跟童话电影里的
似的;后来想当掏粪工,路过粪车就故意拼命闻味儿;后来想当芭蕾舞演员,每天
穿一双前边垫毛线的布鞋练者用脚尖走路。后来我们都各自上了中学,她又开始热
衷于拉手风琴,因为拉的曲调“不健康”,被她中学工宣队收入“三性学习班”,
凡有枪毙人的大会学校都让她去旁听受教育。
文革后她决定养猫,一下养了七只。那时养猫不合法,猫们只好挤在她那一间
屋里吃喝拉撒睡,臭气熏天,好不容易盼到政府下令鼓励市民养猫除耗子,有只猫
一高兴从阳台上跳下去摔断了腿。
“你必须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她再三说。
我在她家过夜,猫们在我肚子上跑来跑去,它们夜里全不睡,从大衣柜顶上往
下跳着玩儿,那我们的肚子当海绵垫儿。砸得我哎哟叫,娃子就哈哈笑。她吃方便
面猫吃红烧鱼,我离婚后她送我一只从黑市上买的狗。
政府还没下令养狗,打狗队天天巡逻,抓到狗必杀。我的狗的名字叫“傻蛋”。
“傻蛋”没权利上街拉屎,我只好训练它把屎拉在一张报纸上。可它不理那张
报纸,非到处乱拉,拉完后跳到我床上一坐,屁股上的屎就沾在我床单上。
“洗澡去!”我把它扔进澡盆,它每次洗完澡都可怜兮兮的发抖、尖叫,趴在
电炉旁流眼泪。
“傻蛋”和我同吃同睡,除了它睡觉的地方它不拉屎,其他地方都拉遍了,有
人告诉我到晚上偷偷带它出去拉,可它从早晨一睁眼就开始一直拉倒晚上,好像直
肠子。
在我离婚后杨飞突然决定结婚前他跑到我这儿来“叙旧”,十年的关系不容易,
他当初用艺术家的傲慢拒绝当我“丈夫”,等我突击结完婚,他又渴望起“家庭”
来,飞快地找了个“妻子”,刚要结婚听说我又离了。
“为什么?”他问我。
“快速过渡法。”我说。
“我怎么办?”
“去结婚吧。”
“快速过渡法”就有一个好处是万事重新开始。杨飞那天晚上决定留下当我的
“情人”。可是到了睡觉时间,“傻蛋”就准时地跳到我床上来。
“去,下去!”杨飞顿时败兴。
“下去吧,傻蛋。”我也说。
“傻蛋”看着我,跳到我身边舔我的脸,然后冲扬飞大叫。
“下去!傻蛋!”我厉声说。
它受了惊,呆住,看着我不动。
“下去!你下去!”
它突然冲着我大叫起来。
我抱起它,把它放在门外,把门锁上。
尽管如此,我和杨飞躺在床上什么也没干。
“傻蛋”在门外叫个不停。
我那点儿起码想向扬飞诉苦的情绪都让它搞没了。
我起来打开门,它飞快地跑进来,跳上床,带着屎臭气死活不下去了。谁碰它
它就叫,然后它拱在我与扬飞之间打呼噜。
“一更里鼓儿催,谁也不认得谁。嗯哎哟,嗯哎哟,哎来哎嗨咿呀,哎来哎嗨
咿呀,嗯哎哎嗨哟……”我梦见大表姑。
“我们还是各自往前走吧。”早晨杨飞起来穿上衣服亲了我脑门子一下就走了。
他再也没来。
我抱着“傻蛋”哭,“傻蛋”不停地打嗝。
“它这么打嗝可不好。”娃子两天后来了。“傻蛋”还在打嗝。
“不知怎么了,是不是吓着了?”我想起哄它下床的事来。
“可怜。”娃子说。
谁可怜?我心里嘀咕,嘴上没说,过两天,“傻蛋”发起烧来,我也发起烧来。
“不好了,我们俩全病了,快来看看吧。”我打电话给娃子。
“什么?它病了?!”娃子的第一反应是“傻蛋”。
“我也病了!我在发烧,我们俩都不停流眼泪。”
“是不是你传染了它?”
“是它传染了我!”
“噢,可怜!”
“要是我们俩都死了呢?”我故意问。
“你死不了。”她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