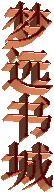
裘山山文集 死者无言
一位朋友死了。
这位朋友的生前好友对我说:“明天在市殡仪馆举行追悼会,你去吗?”
我说:“我去?去吧”
大约是我的语气有些勉强,这位生前好友又说:“因为他是死于意外,所以只
是小范围的搞搞。”
他是想告诉我我在享受特殊待遇。我觉得我应当对此说点儿什么,比如,既是
小范围,为什么要通知我?我与他非亲非故。
可我没能说出什么来。
这是在这位朋友死后的第四天。
我从未到过殡仪馆。我把它想象得阴森可怕。事实上并不如此。我把车寄存好
后,在悼念厅门口的一张桌旁,领了一朵小白花。并学着别人的样子,将小白花素
在胳膊上。白衣服上系白花,一点儿不显眼。
大约有三四十个人来参加悼念仪式。许多人我都认识,我与他们打招呼。
“你来了?”
“你来啦?”
好几个人惊讶地说:你生病了么?脸色那么难看?
我解释说:我总是这样的。最近工作忙了些,没睡好。
这时哀乐响起。追悼会开始了。我不想立即进去,便一个人溜到一边儿看那些
花圈。我想知道都是些什么人在怀念死者。我没料到花圈上的花是用塑料薄膜做的,
年深日久,已老化成黄不黄白不白的颜色,花心积满了灰尘。而且无论是谁死了,
都可以租用它们。只须重新剪两条黄纸写上死者的名字和生者的名字就行。 我看
见了许多熟悉的名字,当然也看见了那位生前好友的名字。
我忽然想,就是这么一个毫无生命的又脏又旧的东西在连接着生者与死者的感
情纽带。幸好,我不用送花圈。
这时有人拽我,我回头,见是那位死者的生前好友。他说:“进去吧!大家都
进去了。”
我便随着他,跟在不长的队列后面,缓缓步入悼念厅,追悼会己经结束,开始
进行遗体告别了。
死者被安放在正中,四周摆了几盆绿色植物和塑料花。大约死在冬天只能拥有
塑料花。队伍走得很慢,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得停下来向死者鞠躬,然后还要绕过遗
体走到左边与亲属们握手。
我站在右边的队列中向左边望去,看见了死者的亲属──老、中、青三个女人,
她们分别为死者的母亲、姐姐和妻子。三个女人正号啕大哭,其中两位还搂作一团。
哀乐淹没了哭声,但淹没不了她们痛不欲生的样子和红肿的眼睛里不断流淌出的污
浊的泪水。
她们之所以哭得如此伤心如此真诚,是因为她们都认为自己对死者的死负有责
任。
我很清楚。
死者的母亲,那位一向种特过度的老女人,此时再也顾不得什么了。虽然依旧
穿着考究,头发一丝不乱,但如果不是她女儿的搀扶,她恐怕早已瘫软在地上。她
的泪水足以冲走60年来的所有往事,却无法冲淡一点点关于儿子的记忆。
5年前,当死者告诉她要与她身旁那位年轻女子成婚时,她以相当激烈的态度反
对,宣布说:如果死者一意孤行,就脱离他们的母子关系,她知道儿子离不开她,
会向她妥协的。
她是位名门之后,丈夫早逝。她一手将一儿一女拉扯成人。就是在吃咸菜穿补
疤的窘迫日子里,她也没有忘记教导他们记住自己的身份。因此她不能容忍儿子带
回一个在“街上”长大的女子,尤其是今天他们又富有之后。这女子的父亲开一家
小杂货铺,门前便是条僻静的街。死者就是买东西时认识她的。眼下她正站在她的
左侧痛哭,泪水滴在同一问灵堂里。
僵死者居然顶住了她的压力,与那“街上的女子”一起租了间农民的房子搬了
出去。这使她的失望和伤心变成了仇恨。
她一字一顿地说:你会后悔的。
儿子一声不响。
她又颤着嗓音说:你是妈妈的全部希望,你是咱们刘家的全部希望呵。
死者依然一声不响。
她在那一刻发誓,要让儿子知道她的厉害。她一步步地逼他,直到他死。
是我害死了他呀我听见老女人在这么想,又一股咸涩苦酸的泪水涌出她的眼眶,
脸颊已被腌渍成了青灰色。死者的姐姐,那位中年妇女,以她微微发胖的身体托住
母亲。滔滔不绝的泪水将她的脸泡成了掺碱过多的黄馒头。
她曾受母亲的委托去那间农民小屋与死者谈判:如果不悬崖.勒马,立即与
那女子分手,他将一无所有。原先在他名份下的那笔存款将不再属于他。
“当然,我不会不管你的。”她加了一句。
死者稍稍有些动摇,因为他知道那笔存款的数目。是他的父亲或者说他的祖父
留下的房产,文革后折合成人民币退赔给了他母亲。母亲将这等钱分成两年存入了
银行,每月取出利息贴补生活。仅从利息他就知道那笔钱的数目有多大。而且母亲
还悄悄告诉过他,他将得到的那笔多于姐姐将得到的那笔。
但这当口,“街上的女子”走到他的身边挽住他的胳膊肘他的姐姐说:“我们
不需要谁的钱,我们自己会挣。你们无论怎样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死者立即消除了那一瞬间的动摇,并为自己的动摇感到羞愧。
这中年女人没有劝自己的弟弟,似乎还表示了赞许。又说了一句:“我不会不
管你们的。”就走掉了。
她知道弟弟是亲手足,她爱弟弟。但她在内心深处却无法抵御占有两份存款的
诱惑。她有两个孩子,老大还是个弱智。是她剥夺了弟弟拥有财产的权力,这财产
本可以救弟弟出泥淖。中年女人哭得披头散发,嗓音嘶哑,令旁观者感动。当然除
了我。
死者的妻子,那位孤独一人站在一旁哭泣,摇摇晃晃没人搀扶没人劝慰的年轻
女子,曾经有着一张十分纯情的面容,她的纯情足以使死者抗拒住母子之情的断裂,
大笔存款的失去,足以使死者忍受住农民土屋星的潮湿、蚊叮虫咬、一日三餐吃青
菜的生活。
但在两年之后,这纯情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仅仅是两年。
他们每日一小吵,隔日一大吵。死者极不善吵骂,因此而砸碎了家中所有的玻
璃杯。他一次又一次痛悔自己的所为。但为了不.让母亲嘲笑,他强忍着没有离婚。
忍了一年之后,他终于无法再忍。我认输,我认错,让她们嘲笑吧。他发疯似
地想。尔后提出了离婚。
这年轻女子非常平静地说:要离婚,可以,给我一笔青春赔偿费。
这青年女子知道死者每月挣多少钱,于是她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数乱按死者的收
入要10年才能攒够。她所以提出这数目没有别的意思,仅仅是想拖住他。她还爱他。
当然是以她的方式爱。
却不料死者竟咬咬牙答应了。
从此他不再是他。他成了个扛长话还债的穷汉子。
是她逼死了他,她心里非常明白。
可我并不想逼死你呀!年轻女子哭诉着,声音含混,只有我能明白。因为如果
让旁边的老女人和中年女人听见了,又会招来一顿痛骂。
有人曾向我描述,人到中年的姐姐那天打开家门时,意外看见了瘦得皮包骨头
的弟弟。
做弟弟的终于无法忍受这没有尽头的折磨,来求救了。他知道那张曾经属于他
的存折上有着大于年轻女子索要的数字。他不惜收起自己的自尊将妻子提出的条件
和自己的困窘告诉了姐姐。他觉得与其忍受妻子的折磨还不如向母亲低头。他相信
母亲会教他的。
做姐姐的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恐怕不好对妈讲。妈最恨她,怎么肯把钱给
她?”
弟弟说:“不给她就永远离不了。那些街道上的干部都站在她一边。我受不了
他们喋喋不休的劝解,我会被他们折磨死的。”
姐姐面有难色,答应把这话告诉妈。
老女人忽然一阵眩晕,有人端来一把椅子让她坐,她执意不肯,伏在女儿的肩
上抽搐,站着。
据说种特的老女人听说儿子低头了,要与那“街上的女子”离婚了,激动得手
直发抖。她摸摸索索地从梳妆台里摸出一支烟点上,一个人靠在紫红色的太师椅上
享受着胜利的喜悦。半晌,她才开口。
“能要那么多?凭她那副样子?”
中年女人忙说:“是啊,我也给小弟说,妈恐怕不会给她。那不太便宜她了吗?”
“小弟自己为什么不来找我?”老女人忽然想到这个问题。她知道她现在要帮
儿子一把是完全可以的,轻而易举的,但她觉得3年来郁积的仇恨不能就这么简单的
了了。她渴望听见儿子亲口说:妈,我错了。
她就忘了她的儿子生了一副与她丈夫一样倔强的脾气,她还不知道她的儿子此
时正为自己的妥协痛苦万分地揪下了一把头发。
中年女人没再为弟弟说话,只是顺从地说:“好的,妈,我叫他自己来我你。”
老女人意外地看了女儿一眼,她以为女儿会说:“算了,妈,原谅小弟吧,他
也是够可怜的。”如果她这样说了,她就原谅他。反正他来拿钱时总要叫她一声
“妈”的。但女儿没这么说。
其实这前后两句话都在中年女人的嘴巴上,出口的刹那舌头自己做了选择。她
至今说不清是什么主宰着这选择。
当她把母亲的话告诉弟弟时,弟弟的脸煞白。那一刻,她后悔万分,她毕竟是
爱弟弟的。于是她连忙说:我再去跟妈谈谈。
弟弟咬着牙说:不,决不。
我忽然想起,年轻女人也曾得到这样的回答。
在这离婚持久战打到第三年时,年轻女人发现丈夫变了,似乎重新对生活充满
信心,对离婚的胜利充满信心。经过打听她得知她的丈夫新近认识了一个女人,这
女人便是他新生的源泉。一股妒意立即进入血液并且循环到每一个部位。她觉得她
越发的不想放弃这个男人了。
那日她特意打扮了一番,从娘家跑到他的住处。他早已搬到单位分给他的住房
里了。
没遇上传说中的女人。但她从房间的收拾和丈夫的眼神中看出这女人的确存在。
丈夫甚至笑着请她坐。她知道如此一来他是肯定要离开她了。
她一声不响,万般温柔贤慧地为他收拾屋子,买菜做饭,还拿出一件刚刚织好
的毛背心给他。当他们像结婚那天一样面对面坐下吃饭时,她非常婉转温柔地提出
想和他恢复关系。
他立即放下碗筷说:“不,决不。”
年轻女人的脸变了色:“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叫第三者插足,休想离婚。”
他又狠狠地摔碎一个杯子,杯子的利碴深嵌进地板胶内,闪着白光。
年轻女人跳过白光说:“早晚我会抓住她的,到那时候,哼,10万也不行!”
“不,决不。”他又斩钉截铁地说出这三个字。
此刻,老、中、青三个女人泪水滂沱。我想她们的肠肠肚肚-一定都已梅成青
色,就是青色也无济于事了。只有大量的泪水的宣泄,能使她们破碎的心稍稍得到
一些滋润,不至于独自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香咽苦酒。
我看着她们如此悲伤便有一种快感。
终于走到了遗体的面前,我是从下往上看的。他的个子挺高,腿很长,身板笔
直,就是太瘦了。白色布一直盖到胸前,露出了黑色毛料西装,看得出是最好的质
地,最好的做工。里面是考究的白衬衣,系着黑色的缎子领带。这不知是她们三个
中哪个女人的意思。其实他喜欢银灰色。大约是化了妆的缘故,脸色比平时好多了,
不再那么黄瘦。头发梳得很整齐,鬃角上的那些白发剃短了成了一片灰白的碴子。
这些白发总是拔了又长长了又拔。额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变得平整。大约没有什么
事可以再让他忧虑,再让他烦躁了。眼晴确确实实闭着。30多年来这双眼睛无数次
闭上又挣开,而这一次是永远闭上了。嘴角为什么微微上翘?看上去有几分笑意。
是死得很愉快吗?很顺利吗?确实,30几年来只有这件事是做得最顺利的──吞下
安眠药之后斜靠在打开了煤气阀门的屋里看书,静静地睡去。
我忽然觉得冷极了,从心脏渗至肌肤,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眼前使幻出一片
冰天雪地。所有的黑色树不都张牙舞爪地伸向天空。雪花纷纷扬扬,以致我的牙齿
里塞满了冰碴。
这时我看见死者的生前好友催促他前面的女人走快一些,这女人在发呆。
这女人之所以发呆,我想大约是因为她在回想六天前她与死者的一段对话。
“恐怕我不能再来了。”她说。
“为什么?”死者急切地问。
女人不回答。
死者又说:“我已经凑够钱了,马上可以办了。”
女人望着窗帘低垂处说:“我跟他谈过了。他说,离婚可以,孩子不能带走。”
“那怕什么?都在一个城市,你可以经常去看孩子。”
女人沉默了一会儿,幽幽地看着死者,说:“我也可以经常来看你。”
死者不再说话。
女人发现他的面目变得十分可怕。但她却是没有想到死的。
死者好一会儿才盯住她说:“是最后一夜吗?”
女人点点头,泪水汹涌而出。死者走过来,抱住她,吻她的泪水。死者在她的
肩上留下一个齿痕。这齿痕现在依然隐隐作痛。
女人在凌晨天蒙蒙亮时悄消离开的,死者是在当天晚上万簌俱寂时死去的。
我看见这女人被催促后挪动了一下脚步。她似乎发现自己还没有鞠躬,就走到
死者的脚下双腿并拢弯下腰去。
在营下腰的刹那,她似乎听见一个声音说:我就知道你不会流一滴泪。
她诧异地抬起头,看看死者又看看周围。没人说话。
她又弯下腰去。
我就知道你不会流一滴泪。
她再弯下腰去。
我就知道你不会流一滴泪。
这女人忽然控制不住自己,发疯似地朝外跑去,跑出悼念厅,又跑到大门口。
死者的生前好友一直在后面紧追不舍。
跨出大门的瞬间,这女人发现一辆吉普飞速驶来,她轻轻地叹了声气,就被吉
普撞倒在地上。
人们立即围拢过来,吉普车的司机也紧张地跑过来。死者的生前好友将女人的
头抱起,大声喊她的名字。
女人睁开眼对他说:“是我害死了他。”这女人便是我。这死者的生前好友便
是我的丈夫。当然,我并没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