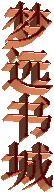
裘山山文集 老树客死他乡
谁也没见过老树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周家拐的人意识到老树存在的时候,它就已经是棵老树了,老得枝繁叶茂,郁郁苍苍。树这种生命与人的最大不同在于,人是越年轻越好看,树是越老越好看。那满身的皱纹,那粗壮的身躯,搁在一个人身上可是要了命了,搁在一棵树身上就是魅力无穷。
故事发生的时候,老树正当年,80岁?90岁?或者100岁?也正当季,是一年中树木最葱茏的季节,5月。所以它的每一根枝条都水汁饱满,每—片叶子都绿得发亮。当然不止是它,周家拐附近的所有树木都如此。上天没赐给周家拐别的什么,就是满山的树木。
当然,老树与其他树还是由差别的,它刚好长在周家拐的村口上,成了村里人进村出村,上山下山,出工收工的必经之地,也成了周家拐的象征。人们一看到老树,就知道周家拐到了。年长日久,老树自然见多识广,知之甚多了。它的德高望重连鸟儿们都知道,纷纷投靠,所以老树身上的鸟窝是最多的,有喜庆的喜鹊,也有不喜庆的乌鸦,它们各自选了枝头栖息,倒也相安无事。老树不知道自已是哪天出生的,还要活到哪天,它就像—条河,一直流淌着,已经陪伴了几代人。它几乎成了周家拐的图腾。
周家拐是个偏僻的山村,刚好被两座山夹着。是它所在的那个县最偏远的一个村子,到县城要走上大半天。由于它的闭塞,它的交通不便,村民们还过着原始的农耕生活。反正人家也不知道山外是什么样子,连见多识广的老树,也以为天下人过的都是这种日子。
但有一天,老树一觉醒来,发现日子变了。
变化是一个年轻人带来的。变化也总是由年轻人带来。
那天老树看见那个年轻人,背着背包提着行李从山外回来了,准确地说,是从部队退伍回来了。他从老树跟前走过时,脚步很急,和村里其他人的脚步很不同。村里人无论是下地还是上山,都是慢条斯理的。反正没人催,也没人比。
老树认得这个年轻人,三年前它曾在这里把他送走,和全村人一起。他是周家拐老村长的儿子。老村长是周家拐里公认的人好人。可惜已经去世了。
年轻人回来没几天,就赶上村里改选村干部。自从田地分到了各家各户,村干部就没人愿意当了,原来的村长是年轻人的叔叔,见侄儿回来了,赶紧推举侄儿。大家也没意见,老村长的儿子呀,又出去见了世面,最合适不过了。
年轻人就积极热情地上了任。
叔叔没料到,侄儿上任后没来请教他这个村长该怎么当,而是很有主见地在老树底下发表了就职演说。就职演说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改变他们这个村子的落后面貌。改变落后面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电拉到他们村里来。侄儿,应该说新村长,在部队已经用惯了电,看惯了电视,简直不能容忍他的家乡还在点松明火把,还过着天一黑就睡大觉的原始生活。
这让叔叔这个原村长有些心烦。在此之前,他家的日子算是富裕的,他为儿子娶媳妇的钱也差也不多攒够了。他早巳习惯了天一黑就和媳妇上床的日子,习惯了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生活方式。他不想折腾,也懒得折腾。有那工夫还不如抽袋烟呢。在周家拐,像原村长这样想法的人很多,他们是按惯性在过日子,对新事物总是持怀疑、迟疑、犹疑的态度:在没看见实实在在的利益之前,他们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新村长就在老树底下召开全村村民大会,进行动员。这也是老树的功能,做周家拐的会场。历届村长通知开会,都习惯说,各家各户去个人到老树那儿说事。“到老树那儿说事”就是开会的意思。
说全村也就是七八户人家,二百来口人,周、吴、郑、王四个姓,所以差不多各家各户都是亲戚。村民大会相当于一个大家庭会议。大叔二伯二舅四婶五姨六姑,嘻嘻哈哈热热闹闹地坐成一片。
新村长站在老树底下,招呼大家安静。他无论是说话口气,姿势,还是脸上的表情,都和老村长像极了。老树看在眼里很是感慨。当年老村长也喜欢在老树底下召开全村大会,不同之处在于,新村长个子比他爹高,抽的是纸烟。再听下去的话,还会发现新村长的口音里夹了些官话。
新村长先说了拉电的好处,晚上娃娃可以看书,大人可以看电视,村里通知事情可以用广播,干旱天可以用机器抽水,磨面粉可以不用人推磨,晚上宰猪草都是亮晃晃的,不会宰到手。等等。总之有了电,他们的日子就可以大变样,可以彻底改变。
有几个年轻人表示赞同。别的不说,他们首先对电视就很向往,去亲戚家时,或者去县城时见过,里面的人又唱又跳,让他们不可思议。虽然他们不能当家,但他们发出了舆论上的支持。原村长的儿子对父亲说,我看过电视机呢,那里面的女人,你一看见就要捂眼睛的。真的,穿的衣服就像没穿一样。他父亲撇撇嘴,吧嗒一口烟,不说话。原村长儿子又说,有了电视机,你就可以天天看电影。周家拐的人电影还是看过的,是县电影队搬了发电机来放的。一年一回,过春节的时候。另—个年轻人对父亲说,拉上电你还能天天看见大人物。他父亲说,我天大看他哪样?大家笑。又一个年轻人说,还能看见外国人呢,金头发,蓝眼睛,鼻子好大,赶我两个那么大。人家笑得更厉害了。笑容里有些动心的样子。
新村长说,乡亲们,这次拉电是个绝好的机会,县里为了实现“村村通”,已经把主线拉到了我们乡里,我们只消拉支线到村里就行了。费用很低的。
有村民说,很少是多少啊?
新村长说,我大概算了一下,二万多不到三万。
有人发出嘘声。
新村长说,二万多就能让我们的村子亮起来,太值了!现在正是大家空闲的时候,劳力也不愁。至于钱,我们只要发个狠,不吃年猪,是能凑够的。我算了—下,一家出三百元就行了。
三百元?三百元可不是小数目。大家不响。
新村长又说,你现在舍不得出钱,将来别人家亮了你家不亮,你连孩子都招呼不到,孩子都上别人家去了。你不信试试?
女人们笑起来,拍拍身边娃娃的脑袋。
新村长说,你莫笑,这是真的呢。临村李家坡都拉好了,以后他们那里亮我们不亮,姑娘都不愿意嫁过来了,都嫁到李家坡去了!国家落后要挨打,我们农民落后就娶不到媳妇。是一个道理呢。
年轻姑娘也悄悄地笑。
新村长接着说,现在这么便宜你不出,将来你自己拉就更贵了,没人帮你了。这次我们是统一分摊,一家三百,做到户户都亮。你以后要自己拉,就不可能那么便宜了,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不少人动心了。
新村长继续说,家家都养儿养女,都希望儿女过得比我们好,你们要相信我,有电和没电是大不一样的,你看人家城里孩子的娃娃,啥子都晓得,啷个晓得的?看电视噢,老师没讲过的他们都知道,聪明完了的。我们这辈子过不好,还让儿女和我们一样么?大家下个决心吧,发个狠吧。我保证你们不会后悔的。
新村长几乎是在哀求人家了。
老树听了他的话都感动了,虽然它不明白电是什么,但它看见新村长这样苦口婆心地劝人家,它相信新村长是为了大家好,就像老村长一样。可是村里这些人是怎么啦,这么听不进去,这么固执?
一个年轻人推推他父亲说,同意喽,赶快同意!
他父亲吧嗒了两口烟说,也不是不可以拉,我是怕现在花钱拉了电,拉来了以后你们又不爱惜。
原村长附和说,可不是呢,当年修水渠,好苦,我大哥带着我们干,把命都丢了,可是看看现在的年轻人,随随便便在水池边上洗头,洗衣服。
另一个老人说,我们那时侯亲属来了,都舍不得给他喝口水,可看看他们现在,舀一瓢水喝一半,就倒掉了。
年轻人不响了.是想起了老村长难过,还是对浪费水感到羞愧?
修水渠的事老树知道得很清楚,那是十年前了,十年前周村吃水困难至极,要到几里外的山里去挑,来回要走五小时。新村长少年时也去挑过,有一次走到半路上累得哭了起来。后来老村长下决心带领全村人修水渠,安炸药时不小心被炸死了。全村人为他安葬,就在老树对面的坡上。现在村里吃水的问题总算解决了。
这时忽然有人开口了,是个老妇人。人家一看,是老村长的老伴,新村长的老母。本来这样的大会,女人是不发言的。但她却是个特别,因为老村长的原因,她在村里享受着特殊的待遇。人家都很敬重她。
老妇人说,要我说呢,大家就发个狠,我们为哪样不把日子过好点呢。我听人家说李家坡拉电的时候,钱很快就收齐了。我们这么不齐心,好丢人的。要不我带个头,我们家出多出一百元。
老妇人的话让大家都害羞了。原村长首先说,嫂子你不要羞我了,哪能让你出那么多?你孤儿寡母的。好吧,一家三百元,我同意。
原村长一表态,其他老人也就默许了。
新村长松了口气。
老树也松了口气。
老树倒是喜欢他们来,他们一来它就热闹了。它对周家拐的每个人都很熟.他们讲话的声音,还有他们叶子烟的味道。不仅是它,连它上面的鸟儿都熟悉他们了,他们来开会,鸟儿们从来不回避,它们也蹲在枝头上听,听个稀奇。
老树见新村长早早就来了,蹲在那儿,有些着急的样子。大概他想,这么个好事,怎么这么不顺啊?原来有细心的人算了一下,把支线拉到他们周家拐,每家用不着出三百元的,只需出二百六十元就够了。为什么新村长要让人家交三百呢?难道新村长还想谋私利不成?
新村长只好跟人家详细解释。他说如果只把电拉到周家拐,那确实是一家出二百六十元就行了,但人家不要忘了,坡上还有五户王姓人家。要把线再从周家拐拉到坡上,就要多花三千元钱了。这三千元一平摊下来,每家就要多出四十元。
村民们听了议论纷纷。
新村长压着嘈杂的声音说,我们周家拐是一家人,就是搬到坡上了也是我们周家拐村里的人,既然是全村拉电,就要家家都亮,不能拉下任何一家。新村长又说,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一起,大家不要太计较了。
老树觉得新村长说得对极了,可为什么大家都不吭声呢?不吭声等于不赞同,老树知道因为那五户王姓人家也在场,所以大家不直说,都沾着亲带着故呢。但会一散,各种意见都出来了,直接冲着新村长去了。
以原村长为首的大多数人认为,多出的那三千元钱应该由五户王姓人家自己出,谁让他们要搬到坡上去,远离集体的?他们免去了低洼地的潮湿阴冷,多晒了太阳,那就该付出代价为什么要让人家平摊?
原村长之所以那么忿忿然,是因为当初王姓人家跟他说想到坡上去建屋时他是不同意的,他说我们世世代代都住在洼里,你们干吗要跑到坡上去?王姓人家说,他们在洼里的位置不好,下雨老是淹水。其实还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和隔壁的郑姓人家不和,最初是因为两家孩子打架,后来女人们吵,再后来男人们打了一架。因为是王姓人家自己执意搬到坡上去的,所以原村长和村里的人多数人都不愿意替他们平摊那三千元钱。
这可难坏了新村长。新村长就挨家挨户地做工作。可是连几个村委的工作都做不通,就不要说普通村民了。王姓人家得知了这种情况,赌气说他们不拉了,他们以后有了钱自己拉。他们还要成立王家坡村。
新村长非常焦急。他怎么能允许在他任职期间出现分裂的局面呢?他又上门去找叔叔做工作。叔叔说,侄儿子,不是我不支持你的工作,是他们自己不得人心嘛。他们想闹独立,那就让他们去独立好了,你还去操那个心干吗?新村长说,叔叔,话不能这样讲。不管当初他们是为了什么搬到坡上去的,我都不能丢下他们不管。我们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叔叔吧嗒着烟不吭声。
新村长说,你也知道,让他们五户人家多出那那三千元,一家就要多出六百元,他们哪有那个能力嘛。
叔叔还是不作声。
新村长又说:叔叔,你给我摆个老实龙门阵,你到底为什么反对。
叔叔停下吧嗒,看了一眼侄儿,说,你也给我摆个老实龙门阵,你坚持这样做,是不是因为你和王贵根家的三丫头梨花在搞对象?你就想让人家都帮他们?
新村长楞了一下,说,你们怎么会这样想嘛,我怎么会呢?
叔叔说,你说你没和她搞对象?
新村长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原来是同学。现在还没谈过这个事。再说我让人家平摊拉电的钱,真的不是为了她,那上面有五户人家,又不是她们一家。虽然咱们村是周吴郑王四个姓,但一直就像一个人家庭一样,我怕为这件事影响了团结。本来就有矛盾,如果这次不把他们一起捎上,以后裂痕就更大了。不团结什么事都搞不好。
叔叔磕磕烟袋,站起来说,就算我支持你,村里还有这么多人反对,我也没办法。
新村长一筹莫展。
第二天天不亮,新村长就出村去县城了。他在县城有战友,他想找战友讨个主意。老树真希望他能讨到主意。天黑尽时新村长回来了,脚步比去的时候轻快了许多。他甚至哼起了在部队上学的歌,老树老远就听见了他的歌,听见了歌里藏着的快乐。
老树也就把皱纹舒展开来了。
第二天,全村人会又在老树底下召开。
新村长说,这次去县城,他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了,既不要全村人多分摊钱,也不让王姓人家多承担费用。
人家都眼巴巴地盯着他,老树也洗耳恭听。
有人说,是不是县里给补助了?新村长说,那倒不是,县里要是给我们补助,别的村个办?摆不平的。
新村长慢腾腾地拿出烟,脸上努力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个年轻人连忙帮他点着火,他抽了一口,才慢悠悠地开口道:我有个战友,退伍后分到县委开车。我去找他的时候,他正陪着省里面来的客人呢,是省城园林局的。来干吗?来买树。现在城里人日子过好了,修了好多新路,但是新路都是光秃秃的,没有树,种了些小树苗也遮不了阳。这样城里人就想出个办法,到我们这些乡坝头来买大树。晓得不?
新村长说着,随手拍了拍他身后的树干。老树吓了一跳:怎么扯到它身上了?它顿时有些紧张。
村民们倒是笑了。大概他们想不到城里人也有不如他们的地方。买大树?要多少,他们有的是。他们从来没把那些树当财产看待。他们只有烧柴的时候会想到它们。
村民们的眼里闪动着光亮,那是难得一见的荣耀和兴奋。有个村民笑道,你们看他像不像他老汉噢!他抽烟哪个样子,好像呢。大家就看着新村长乐,想起了老村长。会场里洋溢着久违的亲情和轻松。
只有老树一下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上。它怎么也没想到新村长带回来的是这样一个办法。卖树?就是卖它和它那些兄弟?但转而它又想,不,就是卖也不会卖它的,他们不会舍得它的。卖了以后人们怎么知道这里是周家拐?卖了以后人们上哪儿开会?卖了以后他们从山上回来在哪儿歇脚?它是他们的一切,是命根子呢。
新村长在人家愉快的笑中说,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情简单,不是有我战友帮忙说话,还轮不到我们村呢。现在他们答应了,明天就先上我们周家拐来。如果他们选上了要买,我们就可以拿这个钱来补充拉电不够的那部分。树是我们全村人的,大家不会有意见吧?
原村长带头说,没意见。一个老人说,树子还那么管钱么?一个年轻人说,如果能卖上几万块,把我们家家的钱全都出了才好呢。
新村长笑说,看把你们美的。
散会了,新村长又把几个村委留下来商量,怎么迎接客人,怎么组织劳力挖树。老树渐渐听明白了,他们果然是打算卖山上那些树,而且他们还想好了卖哪面山上的。老树放心了。它如往常一样沉沉睡去。它不知道这是它最后一夜安稳觉了。
快到晌午时,客人才到。
客人们为了上他们周家拐来还受了些罪,因为有一段路汽车怎么也过不来了,他们只好步行了一段。但是客人们没有白受罪,他们还没进村就笑逐颜开了,因为他们在村口看了老树。他们一眼就看中了那老树。那么粗壮的树干,那么巨人的树冠。他们说他们这一路选过来,就属这一棵最最理想了。树型那么好,那么漂亮,搬回去摆在街心花园里,肯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村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连新村长也是头一次。他们从来不知道树也有漂亮之说,他们以为漂亮只是说女孩子的。他们为自己的树受到夸奖而红了脸,然后笑逐颜开。
开初新村长还有些意外,他看看老树,对客人们说,山上树还多得是,要不上山看看再说?但客人们说他们不想上山了。就是这棵了。新村长想了想,就痛快地说,那好吧,就这棵。我们全力支持。
老树听了浑身颤栗。
劫难真的来临了。昨天它还存有一丝侥幸,希望自己能逃脱,没想到客人们第一个看中的就是它。它以为村里人会舍不得它,会留下它,没想到他们竟那么高兴。他们—点儿也不记得它的好处了吗?他们一点儿也意识不到它的重要性了吗?它不想被卖掉。不管这地方怎么穷怎么苦,并不能影响到它的幸福和惬意,只要有大地、阳光和雨水,它就和别处的树,那些城里的富裕地方的树没什么两样,或许它比它们还更好些,它呼吸到的空气更清新,喝进的雨水更纯净。它熟悉了这里的一切,它目睹老人去世,看着新一代出生,它和这片土地上的人相依为命,换个地方呆会要了它老命的。
但没人征求它的意见。
看着众人欢喜的样子,老树失望至极。这个时候,它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到了新村长的母亲身上。它知道这个村里最最喜欢它的,还是那个老妇人。
记得老村长刚去世那段时间,她总是一个人坐在树下张望,好像还能把他望回来。新村长去当兵后,她也是一个人坐在树下张望,张望邮递员送儿子的信来。后来,村里人都知道她有这个习惯了,有时候找不到她,就会到树下去找。但村里人并不知道另一个更久远的故事,那就是老村长当年是在这棵树下把她迎进村子的。那时老树还不太老,眼神好着呢,连她脸上的红晕都看得清清楚楚。
老树很明白自己在这位老妇人心里的位置,她会舍不得它的。
它期盼着她出现。
新村长把客人领到自己家去了,让母亲杀鸡待客。然后他们坐在院子里,开始商量价钱,商量怎么搬树。老妇人一边做饭一边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她有些忧心地把儿子叫到一边问:他们看中了哪棵树?儿子说,就是村口那棵。老妇人一怔,又问,他们怎么买啊?买上面的树叶吗?儿子说,不是,要把整棵树都买走。老妇人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在她看来,那棵老树就和她屋后的山一样,是不能移动的,一辈子都属于这片土地的。她不能相信,她想儿子大概是逗她。
但是第二天一大早,见儿子真的吆喝着村里最强壮的劳力到村口去挖树时,她慌了。她拦着儿子声音发颤地问,真的要把那棵树挖走?儿子说,当然是真的。她说可是人挪活树挪死,世人都是知道的,树是不能挪的,它会死的。儿子说,那是老话了,现在科技发达,有办法了。老妇人说,我不相信,小树都不好种活,那么大一棵树更难了。儿子说,你放心吧,你想他们出了大价钱,肯定比我们还怕它死呢。一定会有好办法的。儿子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小声对母亲说,你知道他们出多少钱吗?这个数——儿子伸出5根粗粗的指头,每根指头上都是喜悦,在母亲眼前晃了晃。
老妇人呆呆地看着儿子走了。她有些回不过神来,她不知道那五根指头是多少,是五百还是五千。五百也好五千也好,都不能让她开心。她觉得这世道怎么变的,连地上生的东西都会跑走?她的心里跟猫抓似的,最终扔下手上的活儿,赶到村口去了。
等她到村口时,老树已经惨不忍睹了,正无声地哭泣着。
为了方便搬运,它的树冠被砍得七零八落,尸横遍野,只保留了主干。树上的鸟儿更是一大早就被不祥的声音惊醒,逃进山里去了。满地的断枝残叶,散发着树木苦涩的气息。人们兴高采烈地干活,在城里人的指导下一起对树下手,迫切地想把它变成钱,根本没人听见它的哭泣。只有老妇人,遥遥地望着,不敢走近,也不忍走近,躲在人群里难过。—声声的刀斧就像直接砍在她心上,痛得她有些站不稳了。真想大喊一声,你们要干吗?你们给我住手!
但她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她看见她的儿子,从退伍回村后就日渐消瘦的儿子,眉宇间透着快乐和轻松。她不能再让他为难了。再说,就算她喊了,会有人听吗?
老树彻底绝望了。
村里人在专家的指导下,在老树周边挖了个大坑,然后再用稻草将露出的树根一点点缠上。专家一再叮嘱大家小心,不要伤到树根,缠树根时最好连着泥土。整个挖掘工作一直进行到天黑,整棵树总算被挖起出来。为了赶时间,村里人点着油灯和松明火把,又是拖又是拉,把它弄上了卡车。车连夜开走了。
它身后留下一个大坑,就像是挨了炸弹。
人散尽了,老妇人仍站在大坑边上发呆。新村长走过来说,妈,回去吧。老妇人不动,新村长似有所觉,说,等把电拉上了,我在这个地方再种一棵树就是了。老妇人还是不说话,她的心空了。
老树进了城,很快被安置在了人们说的街心花园里。
但它的元气大伤,始终打不起精神来。它站在那儿,冷眼看着城里陌生的一切和令它眼花缭乱的景象,它实在不喜欢这个地方,那么吵闹,那么拥挤,那么热,连空气里都有股难闻的味道。而且它还有个重大发现,城里并不缺树,并不是像新村长说的,路上光秃秃的,所以要它来。实际上城里有很多树,路两边都是,还有一些不长叶子但是夜里会亮起来的树,亮得它无法入睡。
也不能说城里人对它不好,他们把它种进街心花园后,还怕它站不稳,用竹竿四面架着它,并时不时地给它浇点儿水。但问题的问题是,它受的伤害太大了,失去的水分太多了,这些措施已无法补救。进城没多久,天气就热起来,城里的日头比山里毒许多,而且日头晒到地上,地上是水泥和沥青,又更毒地返射上来,干蒸着老树,蒸得它喉咙发干,心里发毛,满身的断枝怎么也抗不住日头的烤晒。没多久,仅存的一些叶子也黄了,一张张飘落在地。
老树感到自己气息奄奄,加上浑身捆绑的竹竿和光秃秃的头,又令它羞愧不已,它老树什么时候这么狼狈过?这么时候这么颓败过?它无比怀念它的故乡周家拐,怀念山里的清净和凉爽,也怀念老妇人临走时那不舍的目光。
昏黄时,城里人光着胳膊光着腿,到街心花园来乘凉。因为有夜里会亮的树,他们在街心花园总是呆到大半夜,他们摇着扇子,聊着天,打着牌。但无论来再多的人,也没人会看上老树一眼,并不像新村长说的,城里人会把它当宝贝。只是有一次,它听见一个女人惊讶地说,呀,这树好像不行了。但她也只是说说而已,她都没有顺手把她喝剩的半瓶水倒给它,而它是多么需要水啊,它觉得自己迟早会干死掉的。
这天黄昏,经过太阳一天的暴晒,整个城市都蔫唧唧的,空气里全是汗臭。虽说已经立秋了,但城里人还是叫苦不迭,说秋老虎真厉害。如果是在周家拐,哪有什么秋老虎,—上秋之后就雨水淅沥,舒适得很。大街上洒水车来来回回地洒水,试图使空气略微湿润些。但在毒日头下站了一天,满身创伤的老树像被人忘了似的,继续在干渴中苟延残喘。它感觉昏昏沉沉,度时如年。它不知道自己还能捱多久,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到来年春天。它悲哀地想,自己也许要客死他乡了。
傍晚,当城里人又光着胳膊光着腿来街心花园乘凉时,老树突然眼睛一亮:它看见了老妇人!看见了那个在这个世上唯一在乎它的人!它不明白她怎么会来?她来做什么?
老妇人也看见了老树,她一定认出了它,因为她马上就跌跌撞撞地跑过来,绕过那些竹竿支架一直跑到树下,用她的老手一遍遍地摩挲着树干,眼里满是泪水。她一定没想到老树会变成这样,一定没想到老树会这么凄惨,像个浑身缠满绷带的重伤员。叶子掉光了,连树干都开始干瘪,难看得不成样子。
但她还认得它。她怎么会不认得它呢?它几乎伴随她度过了一生。老树走后她寝食难安,她茶饭不思,她日渐消瘦。新村长无奈,只好送她到省城来。也许她是这样进城的;老妇人来了之后,就大街小巷地找,她发誓要找到它,只要看到它在城里活得很好,她就放心了。她要告诉它他们周家拐终于拉上电了,包括坡上的5户王姓人家。原村长家还买了电视。村民从电视里见到了省城,他们惊愕地张大了嘴,他们打死也想不出城里原来是这样的,像另一个世界。几个年轻人终于经不住诱惑,到省城来打工了。老妇人就跟着他们一起到了省城,也许她是这样的进城的;但周家拐就是周家拐,一个月后乡里来收电费,每家几十块的电费又让村民们心疼不已,许多人家又不再点灯了,重新用起了煤油灯。原村长就动员新村长再卖些树,既然一棵老树能卖那么多钱(听说他们还卖便宜了),那山上的树不是多得是吗?
老妇人一听说儿子还要卖树,再也无法忍耐了,和儿子吵了起来。老妇人说,我死也不呆在一个没树的地方,你要卖树我就走,她一气之下就走了。也许她是这样的进城的。
不管老妇人是怎么来的,总之她来了,她是为老树而来。她一遍遍摩挲着老树,两手发抖。她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老树会变成这个样子,要是知道,她是打死也不会同意他们把它弄进城里来的。她就是把眼泪流干,也无法把它浇灌得生机勃勃了。如果是个孩子,她一定会抱上他就走的。可现在她却万般无奈。因为周家拐才是它的母亲。它已经离开了母亲。
老妇人四下里寻着什么。老树注意到,凡是有喝水的人路过,她就盯着别人。老树明白她是渴了。这么热的天,再多的水也不够喝。果然,当老妇人看见一个小男孩儿将一个瓶子丢进路边的垃圾桶时,她连忙跑去拣了起来。但她没有喝,而是急急忙忙跑过来,把剩下的小半瓶水倒在了老树的根上。
老树干涩的眼里已流不出泪来。
这时,一辆三轮车载着两个年轻姑娘路过,其中一个姑娘一边打着手机一边嬉笑着,将喝剩的半瓶水朝路边那么一丢。瓶子骨碌骨碌地滚到了路中间。老妇人一见,急急地跑过去拣,一辆出租车飞驶而来她竟没看见,也许那一刻她眼里只有那个瓶子了,她几乎是朝那辆出租车扑过去的。她当即被撞倒在地。
啊——有人惊呼:撞着人了!
马路上顿时冒出了成百上千的人,把出租车和老妇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得严严实实,老树什么也看不见。它焦急万分,不知道老妇人到底怎么样了。警车来了,警察来了,路人纷纷向警察说当时的情形,却没人能说得清,因为没人注意到出事之前老妇人在干什么,没人知道她为什么要冲向马路。
只有老树知道。因为它亲眼目睹。
但此刻它悲哀地站在暮色中,已经彻底不行了。临终前它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也许老妇人也会和它一样客死他乡,那么,他们就彼此作个伴儿吧。
2002年9月,成都北较场